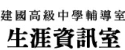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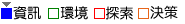 
|
|
|
隨時隨地假戲真作
只要表演欲一發作,我不是跑到百貨公司櫥窗辦假人,就市當街眼起吵架的情節,恨不得詔告天下──我是不折不扣的戲劇系學生。
「你好,我唸戲劇系。」當我第一次離家到關渡讀大學時,這句話就常掛在我的嘴邊。我秉持「初生之犢不畏虎」的信心,盡量用最清脆嘹亮的聲音自我介紹,希望這個地方快點熟識我。我住宿舍的第一個晚上,將過往對這個學校、這個科系所有夢想再複習一遍,不禁躲進被窩偷偷地笑了。
然而,當夢想遇到現實,卻是破碎的開始。
班上同學都有「顯赫」的來頭,閃耀著比太陽更令人睜不開眼的光芒,令黯淡的我想隨著舞台的布幕一同隱去。課程的安排都是要在眾人面前表演,挖出自己的心事,及最不想被提及的舊傷口,我心中時常為此掙扎,卻也再不想坦承的時刻等著挨一頓好罵。
而系上學長姊美的、醜的、怪的一應俱全,真可說是個「動物園」。有的親切,有的只活在自己的世界,就有個學長宣稱他已得了不治之症,隨時都可能死掉;有個學長愛川五彩繽紛的緊身褲,脖子圍了一圈羽毛,帶著耳機邊走邊跳舞。我的羞澀在他們面前相形見拙,加上獨自生活的種種問題,不禁時常躲在被窩中啜泣,此時,聽到鄰床的同學也在低泣,我才知道,這巨大的衝擊不是只有我感受到了,也因此我結交第一個好朋友。
當我逐漸融入這個環境後,不禁愛上這裡,並相信有一天我能真的如魚得水。完全陌生的國劇課中,我咬著牙訓練僵硬的四肢,肉體上的疼痛使我腦中一片空白,斗大的汗水不停滴落。而劇本導讀老師的超強記憶力和一絲不茍的要求,讓我在期中考得五十九分後不敢掉以輕心,他要我們看的電影,即使忙到半夜也要趕緊騎車殺到西門町去看,坐在電影院的軟椅吹著冷氣時,眼皮長不由自主地低垂,猛然驚醒時,還會看到半夢半醒的同學。
在說到堂數最多的表演排演課,老師雖然蒼白瘦弱,罵人可一點也不含糊,丹田十分有力,原本四小時的課,長無線延伸到半夜,隔日在加課。老師不僅上課認真,還要批改每週固定的報告,我想他大概真的「一天只睡一個小時」吧!
最難的是肢體接觸的課程,老師要我們拋開性別的限制,在指令下擁抱或作其他動作。第一次上課我完全不知所措,從小接受的教條要在一瞬間打破,我為此調適了好久,在排戲過程中,當飾演丈夫的男同學深情款款望著我時,我不停提醒自己:「這只是戲!」才沒有愛上他。
一段日子過後,我不論是和同學出去看表演或閒逛,都有種深深的感覺:「別人好怪,這個世界不太真實。」控制不了的表演欲隨時都發作,跑到百貨公司櫥窗當假人,或當街眼起吵架的情節,恨不得頭上頂個聚光燈,詔告天下:我是不折不扣的戲劇系學生。老師知道後,面帶微笑說:「是你們怪不是別人怪。」同學之間的感情很像患難之交,平日無閒聊天,都是靠排戲的互動維繫感情。有時候排系排到三更半夜,一群人神智不清的「爬」出系管,在美的驚人的星空下走回宿舍,才發現大門深鎖,只好隨便坐在階梯上和流浪狗一起睡。
除了表演,我們還要學習製作佈景、服裝,生活在「處處皆藝術」的校園,更是十分享受。清晨看穠纖合度的舞蹈系同學打太極拳,聽音樂系傳出的悠揚琴聲〈有時是挺嚇人的〉,看美術系擺在系館外的裝置美術,然後到學校義大利餐廳看名人,晚上去山頂看捷運站的燈火,睡不著只要走向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戲劇系管就對了。
我不在乎在戲劇中找到了自己,抑或是迷失了自己,只知道夢想和現實正在握手言好,或許就像我們演出時的最大挑戰吧──不管觀眾如何反應,戲劇都要演到落幕!
| 台北市立建國中學輔導室生涯資訊室製作。 本頁推薦使用FireFox瀏覽器閱讀. Copyright© 2002-19, 建中輔導室生涯資訊室. 寄信給網頁維護人員 / 建國中學輔導室首頁 / 建國中學首頁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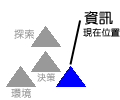 |